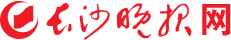散文 | 腊月里甑酒
■朱鹏飞
老家的年很长,进入腊月,空气中都飘着年味了。甑酒、打糍粑、杀猪、磨豆腐、捞鱼、做年饭……大人们年复一年、有条不紊将生活向着年节推进。现在,又临年关了。
米酒是老家最好的待客之物。女人早做好了准备,发酵半个月之久的酒糟,正待外出搞副业的男人回家甑酒。年关接近,赚钱的、赔本的男人从四面八方赶回了家。
一场雨雪,阻碍着勤劳的乡亲们外出,正好甑酒。堂屋中搭个土砖灶,架好甑酒的专门工具。下面烧水的锅叫地锅,倒入酒糟,加水拌匀。地锅上放着木质甑桶,甑桶上顶着天锅。天锅里装满冰冷的井水,用来冷凝酒,接口处用湿布封好防止漏气。
红通通的柴火烧起来,酒糟煮沸得翻滚,含酒精的蒸汽遇天锅冷凝成米酒,顺着漏斗状的天锅汇聚到集酒沟,经导酒管流入酒坛。父亲在世时,春节我家至少得备上两坛酒。
农历十二月里烧火,暖和,还有口福。母亲从地窖中取出红薯,在火炉中煨几个香喷喷的红薯。同时拿报纸包几个鸡蛋,用冷水将报纸打湿,放入火中,十余分钟,火中一声声爆炸,鸡蛋熟了,母亲说小孩子吃了这鸡蛋利尿。几兄妹抢煨鸡蛋吃,吃完,再抢红薯吃,争得哭哭啼啼,马上又破涕为笑,嘻嘻哈哈。别家的妈妈也拿来了鸡蛋、红薯煨给孩子解馋。
热水需要不断地换成冷水,孩子们来一次冬天里难得的洗澡。热水太多,母亲站在堂屋门口,大肆吆喝:“谁家要热水啰,赶快来提哦。”乡里乡亲不讲客气,提着水桶来取热水。
伴着天锅里的冷水升温成热水,酒香从村头飘到村尾,甘甜清香的酒味把男人们吸引过来了。三五个男人围堵着灶门,添柴、烤火、扯谈、试酒。热酒最容易跑了酒气,母亲紧紧地捂住酒坛接口处的棉絮。她一转背,父亲又从酒坛中舀出酒来。三五两酒落肚后,男人们红着脸膛、硬着脖子讲述一年来的经历,斗狠,吹捧,海阔天空、不亦乐乎。身子越来越往火边靠,然后自嘲:当官不怕高,烤火不怕低。
书香伴着酒香飘。一次年前甑酒,正读完一本对联故事书,我现炒现卖:前清一位科举考生,殿试中皇上问他祖辈和父母是做什么的。考生为难,不好明说,便用联语兼谜语回答——祖母:玉甑蒸开天地眼;祖父:金槌敲动帝王心。父在外,肩挑日月;母居家,扭转乾坤。大人们思索一下:祖母酿酒,祖父弹棉花,母亲磨豆腐,父亲挑担卖豆腐。乡里人猜这种谜语易如反掌,这些事乡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对联调动了大家兴致,要求我追加故事。我一口气背了四五十副对联,大家都夸我记性好。乡亲们读书少,日常的学习就是红白喜事上的对联。祖先神龛上那几副经典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承先祖一脉相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个个都把它当家风,记住。如今,老家遇红白喜事,还有人电话和我斟酌、推敲联语的事。
上大学后,一直在长沙生活,每次年关我回到家已是年三十,家中米酒已经备好。让人忧虑的是,看到的几乎都是这幅图:起得特早的父亲蹲坐在火炉边的小凳上,猫着腰。双腿夹着火炉,双手遮着火炉烤火,火炉上一把铁壸正温酒。父亲嘴里叼根烟,边吸烟边喝酒,烟雾上腾的那个眼睛眯着,享受。
米酒度数不高,父亲在家的日子,从早喝到晚。春节里拜年的客人连线,给父亲名正言顺喝酒的理由。不论大小,一进门父亲就说:“喝点酒,喝点酒,我陪你喝。”能喝的客人不喝,就是看不起主人。
我劝父亲戒烟戒酒,他说只能和生命一起戒掉。他还说:不用操心子女了,没烦恼,早上起来喝点小酒,暖暖身子。父亲不善言语,无欲无求,从没给过我麻烦或主动打电话给我,每次接电话,不出三句话就挂机了。我想,烟酒陪伴他,他才会不孤独,便不再提戒烟戒酒之事。
66岁的父亲生病了,我知道一盏油灯即将耗尽。经检查,出了结果。父亲说生死对他来说不重要了,不麻烦子女,坚决放弃住院治疗。在长沙我家,病痛和烟瘾酒瘾的折磨,让他度过了生命中最难熬的两个月。
我们这代人甑酒磨豆腐的活儿大多没有传承,交给了专门作坊。以前家家户户过年甑酒磨豆腐的场景难现了,如今,在老家也只能偶尔见到。我常常怀念那热乎乎的煨鸡蛋、喷香的烤红薯、沉淀后的酒故事和浓浓的年味,以及嗜酒如命又戒不掉、内心孤独的父亲。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