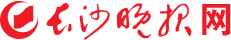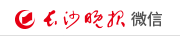散文 | 旧年
■胡晓江
仪式隆重的除夕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来了。孩子们的眸子亮过屋子里的灯盏。
从中午开始筹划的那顿团圆饭,直到向晚时分才端上桌子。父母满意地瞅着满桌子的菜肴和垂涎的一圈儿女,轻轻捶打着酸痛的腰肢。只有他们最清楚,这一桌饭菜的筹划时间不是半天,而是过去的整整一年。一家老小将以大快朵颐的方式,告别旧年的离去,迎迓新年的肇始。
此前的一些时日,父母就张罗着过年了。修屋沟、铲枯草、打扬尘、扫猪圈、贴春联、粘窗花。还为孩子们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袜。青花瓷坛里装得满满的,油炸红薯片、炒花生、炒南瓜子都有。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院子里清清爽爽。饭桌前,放着一条板凳,板凳上搁着碗筷。整块的鱼肉,刚刚蒸熟还冒着热气的鱼肉,翘出了碗边。还有两碗喷香的米饭,两杯浓俨的烟茶,两盏晶莹剔透的烈酒。鱼肉间,立着一只量米的竹筒,盛满米粒,米粒上插着一炷燃着的檀香。那些鱼肉,是敬天、敬地、敬列祖列宗的,只有敬过了天地祖宗,磕了头、打了卦、焚了香,一家老小才能开吃。
那是一年一度最郑重其事的吃饭了。母亲满脸和煦,轻言细语,连一向严肃的父亲也眉眼舒展,嘴角挂着淡淡的笑靥。父亲端坐在方桌的上席,他的身后是堂屋正壁上“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父亲用简短而粗俗的话语,为过去的一年做着言简意赅的总结,他说到了小孩,说到了谷子,说到了猪圈,说到了祖坟。边说边抿一口白酒。他说得颠三倒四,不紧不慢,像是自言自语。一堆的话语,以“多吃点,多吃点”作为结尾。
那也是一年一度最郑重其事的烤火了。没有电视,没有电视上的春晚,甚至没有电。一盆兜根火熊熊燃烧,火焰之上是铜质的吊壶,黑乎乎的铸铁吊钩,一串串的腊肉、腊鱼。 火中是松树的兜根,油茶树的兜根,燃烧时有着松脂的清芬和茶碱的气息。火,吐着红艳艳的舌头,冒着淡蓝色的烟缕,火苗打着旋儿,烟缕袅娜着。兜根“噗噗”燃着,母亲说,那是火在笑。
火焰腾跃着,铜质的吊壶黑乎乎的,水开了,弯嘴处冒着热气,壶盖被一下一下地掀着,打出清脆的节奏。火光映照着膝盖、张开的手掌、皮影戏一般红红的脸颊,映照着父亲、母亲,一圈的儿女。父亲在胸兜里掏着什么,孩子们懂得那将是这个晚上的华彩部分——给压岁钱。孩子们屏声静气,静待着慈祥的父亲将角票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一个地递到自己的手上。父亲会将角票在胸前烫一下,使角票平整妥帖了,甚至还要甩一甩,甩出一点儿声响,才会递到孩子们的手上。
夜已很深了,母亲说,睡吧,都去睡吧,我们大人来守岁。孩子们尽管被瞌睡虫侵袭,坐在木椅上个个东倒西歪,仍坚持着要守岁。他们要看着旧年的最后一秒悄悄过去,看着新年的最早一声“嘀嗒”悄悄来临。
迷迷糊糊中,村头依稀有了鞭炮的炸响。父母说,该“出天行”、该“开财门”的时辰了。父亲手上捏着一挂千响鞭炮,打开堂屋厚重宽大的木门,走出阶沿,走到地坪,看向深冬幽邃的天宇。然后他点燃鞭炮,让“噼噼啪啪”的轰鸣应和着远远近近的鞭炮声。
木椅上东倒西歪的孩子们被惊醒了,像箭一样被弹射出去,在地坪里欢呼雀跃。
大年初一天明,孩子们起得特晚。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满地红红的鞭炮碎屑,意识到新的一年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了。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