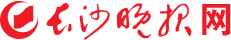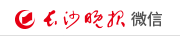麓山浩然
彭璐珞
麓山名列南岳七十二峰之末,高不过三百米,却被称为“长沙的名片”。凡旅经长沙者,必来此一游;长居于此的本地人,亦年年岁岁,游之不厌。于是,一到周末假日,天气晴明之时,总见人群如织如梭,摩肩接踵而上,熙攘连衽而下。然而,到得山中,虽然身边人头攒动,却不觉烦扰逼仄,仍有清气沁人,身心旷然。
山不高而名,如有大泽深山龙虎气;人虽多而静,总觉清风拂面来。麓山,何以能如此?
麓山门两侧,有一对长联。我日日打门前过,却不曾留意。有一天,迎着晨光,这两行字突然入得眼来,直击心底:学正朱张一代文风光大麓,勋高黄蔡千秋浩气壮名山。
麓山有文脉。
这文脉,会聚在山间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孟的儒学正脉,至南宋时,一代儒宗朱熹和岳麓书院山长张栻曾在此会讲,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会讲三日三夜未曾停歇,一时车马之众,瞬间饮干了书院门前的池水,弦诵之声洋溢,远近可闻。
麓山的文脉,从来是游人向往的。即使不明白何谓“道南正脉”,何谓“潇湘槐市”,只因了这千年学府的盛名,便吸引了无数人翘首前来,观瞻留影。然而,如若仅有文脉,麓山还不足以有如此气象。文气清雅,却常失之于柔弱;麓山的气象,却是清中有刚,所谓“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这巍巍气象是因为,麓山还有武魂。
行在山间,总有小路通幽,尽头常是烈士墓冢。小小一座麓山,掩埋了上百名仁人志士的忠骨。勇开民国的黄兴,拔剑南天的蔡锷,蹈海殉身的陈天华,实业救国的禹之谟……还有众多北伐志士、辛亥英烈,抗日忠魂……累累忠骨相连,堪称一整部中国近代史。
文华武英,尽萃山中。他们上马杀敌,下马露布;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东晋陶侃,在麓山植杉结庵读书,射杀巨蟒,为民除害。北宋胡寅,一介文士,怒斥奸臣,大义凛然。
何能耳?若要一言以蔽之,便是山门联中的“浩然正气”。
浩然正气,是怎样一种气?
亚圣孟子曾这样形容: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文天祥《正气歌》里这样描绘: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这气宏大。它上薄云天,下履厚土,充贯天地,恢弘磅礴。它的格局是家国天下,它的纵深是千秋万古;在它面前,一切小情小调都相形见绌。这气刚健。它刚而不柔,健而不媚,大雄大力。以五行而言属金,如金石铿锵,掷地有声。一如埋骨岳麓的护国将军蔡锷,二十三岁,练兵长沙,戎装驱马,直上岳麓峰巅。随后南天剑起,以一隅而抗全国,“明知无望,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这气正直。它直而不曲,正而不屈,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它是鲁迅说的“中国的脊梁”,是曾国藩“撑起两根穷骨头”,是元军铁骑攻破长沙时,岳麓书院数百书生赤手空拳相抗的壮烈,“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缆林木者,累累相比。”
这气非勇悍。燕国勇士秦舞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忤视。齐国勇士北宫黝,人刺其肌肤,不为挠却;人刺其目,而不转睛。霸王项羽,力可拔山,叱咤自雄。飞将吕布,骁勇绝尘,纵横淮泗,无人能敌。然而,他们都是气血之勇、匹夫之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如若徒有勇悍而无仁义,则也不过是刺客、任侠、乃至莽夫而已。这气非戾气。正气有雷霆万钧之力,可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然而,天地间另有一种戾气、邪气,也可风卷残云,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真正的浩然正气必然“配义与道”,顺乎天理,合乎仁义。合于道,则伏尸百万,血溅三尺不为过,如《诗经》盛赞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浩然正气,可以养生,百邪不侵,众病不扰。文天祥被元人拘禁在狭窄阴暗的元大都监狱中,有潮湿浮动的水气,蒸熏沉沤的土气,暴热堵塞的日气,炎热燥人的火气,陈厚发霉的米气,腥臊汗臭的人气,腐败污浊的秽气。然而,他以孱弱之身处其中两年,却无恙无病,原因何在?只因自身存养一股凛冽浩然的正气,便可“以一正气而敌七气”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王阳明被贬贵州布政司龙场驿,此地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贬谪来的中原人士,不过数日已曝尸于途;而他居此三年,却毫发无损,乃至悟得大道,只因始终禀一股堂堂正气,坦荡光明,“未尝一日之戚戚也”。
浩然正气,可以格天,光明磊落,神钦鬼服。“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中国人的神并非天降,而由人修得,忠臣孝子,生而正直,死后为神。关羽、张飞,秦叔宝、尉迟敬德,皆以英勇而封为武圣,位列门神,除妖镇邪。《辽史》记载,王鼎正直不阿,某日休息时,忽有暴风雨将他的卧榻卷入空中,他毫无惧色,高声说:“我是朝中端正之士,邪不干正,请慢慢把我放下来”。须臾之间,风停雨歇,卧榻复归原处。同时,浩然正气,可以治国,政通人和,海晏河清。中国古人早就深知“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来自天地,涵于人身,却并非天生,而是需要“存养”,直到“充实而有光辉”。如何存养?
一曰身正。
人之初,性本善,正气的存养从孩童的启蒙教育开始。《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孩童八岁入小学,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从涓滴小事开始,“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以身体的中正涵养内心的方正,行动揖让,一切都有节度。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六艺之学,知朝廷君臣之礼,穷理尽性以至於命。
人身之中,胆为中正之官,夜里十一点至一点当值。夜间早睡,可养中正之气。睡醒后,天未亮时,初睁眼,心中坦然,无所挂虑,孟子称之为“平旦之气”,善养此平旦之气,也可减少六欲之干扰,增添心地之清明。曾国藩将静坐列为每日功课之一,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二曰心正。
止一为正。一是天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心应当法于天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若心汲于私欲,溺于情绪,则与正气隔绝。《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放下一己之私,心怀家国天下,久而久之,气象自然刚正,自然恢弘。一也是精一。正心必得精一,心无散乱,念念在兹,既不忘失,也不助长,如春夏秋冬,四时推移,而成岁月;如水滴石穿,日久功成。曾国藩有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三曰行正。
孟子论正气之养:“是集义所生也,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义者宜也,行所当行,便是集义。正气来自不断积累合乎义理的行动,首先要有行动,蒙以养正,强调果行;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如若不行,则难免沦落为袖手空谈。其次,行动需要循道、合理,理直则气壮;若有一件事不合道义,理便有亏,气便会馁。再次,义要“集”,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如若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无法养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从湖南大学到岳麓山,需行过“自卑亭”,途经“登高路”,暗含《中庸》“譬如登高必自卑也”的深意。最后,集义并非袭义,如果道貌岸然,假仁义之名而行功利之实、“热衷人作冰雪语”,则不过是“义袭”,正如那个拔苗助长的宋人,非但无益,反受其害。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