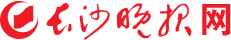金捞坝的金秋
哈吾斯力汗·哈斯木汗
金捞坝,是我脐带血滴下的地方。
虽然我离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长达几十年,可对它的思念不但没有淡化,反而魂牵梦萦。
你在讲述自己所思念的对象时,别人是通过你的表情、语气和情绪的变化来估量你的思念程度的,其实,思念是别人看不到而自己能看清、存储于心底的纪录片。
如同新疆的其他草原,整个金捞坝村民的冬季准备也在秋季开始。割草活动一开始,我就知晓秋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那时候,我常常跟着父亲去冬牧场。
我们到冬窝子,父亲取下挂在木屋顶上的钐镰,放在槽牙形状的砧子上锻打,拿着一根草,反复试刀刃。调整好钐镰靶子中间的把手,绑紧把手的皮绳,坐在草地上开始用磨刀石不慌不忙地磨砺着刀刃。父亲做完这些事,太阳也升高,花草上的露水也云消雾散。
父亲挥舞着锐利的钐镰,倾听着花草被切割时发出的“咔嚓”声,正在割草时,被割草声惊吓的蓝翅蟋蟀在父亲的两边飞来飞去。
父亲从口袋里拿出皱巴巴的手绢,擦着从额头流下的无数汗珠,拿着放在草堆下的酸奶皮囊,一口气喝下一碗说:“孩子,酸奶快热了,放在阴凉的地方吧。孩子,你也要学会割草,但是我希望你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参加工作,当国家干部。”
练习使用钐镰割草前,我的首要任务是:翻一翻父亲割下干枯的草;把完全枯萎的草堆起来;从小溪提水,用地炉子烧茶。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我偶尔从田地里挖来几个土豆,用热火灰埋下,烤熟。那时候,土豆是我们家的蔬菜。我想多挖几个土豆,父亲不愿意,常说一则谚语:“如有半天的生命,必备一天的食物。”
太阳领着晚霞最后一束光,翻下叫“窄路沟”的山丘,夏牧场那边肃立的灰黑山峰渐渐消失。
被温暖的阳光陶醉的山丘、山脊和草原,慢慢变灰白,最后变得灰黑。父亲发现时候不早了,就把钐镰放进木屋,收拾东西,把马鞍放在马背上,准备回夏牧场。父亲骑上马,我坐在父亲的后面,两手抓紧后鞍绳,脸靠父亲的背,问这问那,往夏牧场进发。
一到秋天,整个金捞坝的草原犹如掉了色的地毯,失去绿油油颜色。绿绿的山丘就像冬天放在外面的牛肺,显得灰白。人和畜牧都在向往气候暖和、草丛茂盛的另一个地方——冬牧场。我们家对面森林中马鹿的嚎叫声和牛的嘶鸣,汇聚在一起,在深深的山沟里回荡许久。
“看看它们毡房顶圈那么大的角。”父亲指着那些马鹿对我们说:“开春我寻找马鹿,这些鹿角应该属于我。”这时,父亲的小胡子微动,眼中显出期望。父亲每年开春都去覆盖积雪的草原寻找鹿角,那些年,父亲靠鹿角至少能赚一千多元。
是金捞坝进入金秋的季节。
深红的野蔷薇果,嘟着嘴,下垂着。干枯的桦树皮开始蓬松,翻出了紫红的里子。花楸的果子恍如断了线的红色珍珠,撒满在地上。林子里是五颜六色的世界,简直是一幅美丽的油画。
一旦马匹用缰绳拴于马桩上,虻虫让它不得安稳;我坐在离木屋不远的山丘上,时刻观察母亲的行为。母亲一旦进屋,准备偷走奶酪或奶疙瘩的乌鸦姿态轻盈,在娇艳的花丛中穿梭往来,五颜六色的丝绸翅膀蝴蝶络绎不绝;坐在花冠的一边,头伸进花朵中间,拼命地吸吮糖汁的胡蜂,都不见了。牛已经摆脱了牛蚊子的骚扰,甩动尾巴,埋头专心致志地吃草。夏天,两腮鼓鼓地咀嚼着的那些调皮的犊牛,找不到吃的花草,无可奈何地望着冬窝子,静静地站着。看来,习惯于夏天的它们厌倦了这个秋天。
立秋后,金捞坝的天气渐渐凉了。到处弥漫着秋天的气息。秋天冰凉的风从门缝、木屋墩子的间隙、门槛底下进入房屋时,我们家在地炉子里生火的日子告一段落,开始在木屋里的铁炉子里加火。孩子们常到森林里去拾木柴时玩打松塔仗。新鲜的松塔打在脸上,很疼,我们往往不欢而散。在林子里,把干枯的松塔拿在手中,轻轻一拍,就可以看到有单翅的松子。真的很奇怪,掉在地上的松子,凭着自己的翅膀,飞往远处。后来才知道,松树凭这个单翅松子来实现繁殖。
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有不同的思念。有些人默默地藏在心底,有些人喜欢说出来。不管怎么样,对脐带血滴下的故乡,留下童年美好回忆家乡的思念绝不会停下。没有厚爱的地方就不会有思念。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