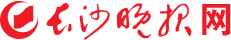三平方米
周玲
人群缓慢地向前挪动,那蚂蚁般排队搬运食物的景象,在老街入口处每天至少要上演几回。这次我被卡在入口处的楼梯上,后脚挨着前脚,各种难以言喻的气味混杂着钻入鼻孔。依稀可以辨别到其中的孜然味,是右前方卖烤鸡腿的那个小摊传来的,摊主正光着膀子往转动的烤架上撒着孜然粉。
烤架上的鸡腿转动着,我的思绪也跟着转动,回到幼时的记忆。几乎整个小学阶段,我的时光大多是在那所“藏在居民楼里”的小学和校门口那条走路经常被绊倒的老街度过。每天清晨,老街上便会挤着许多卖菜的小摊,这些摊主多是老人,拿个塑料布往街边一铺,把各种小菜往上一摆,这便是简易的卖菜摊子。送完孩子上学的家长大多会顺手在菜摊上买点小菜带回去,于是,老街这个时候成了一小型菜市场。
而放学铃一响,老街却是另一番景象。卖菜的小摊都散了,换上来的是各种小吃摊,然后是一大片校服蓝呼啦啦地涌向小吃摊,那些背着花色书包的小学生手里攥着一些零钱,踮着脚扒拉在小摊边缘,亮晶晶的眼睛直盯着摊上的小吃不放……夕阳的余晖下,老街是小学生的“快乐天堂”。
我时常去的是老街拐角处那家烤串摊。差不多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卖烤串的摊贩,就那样一个三平方米的移动小摊,也不管正不正宗,路过时闻着那股孜然混着牛羊肉的焦香,总会忍不住买上几串。
那几年的零花钱几乎都喂给了小摊上的牛肉串,去的次数多了,摊主夫妻俩都认熟了我的脸,每次远远地看见我蹦跳着过来,便笑着和我打招呼。摊主大叔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围裙,上面沾着油渍,阿姨则围条碎花头巾,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穿串,案板边永远堆着小山似的肉串。
有回我踮脚递钱,大叔往纸包里装串时忽然问:“你怎么从来不吃羊肉?”我说对羊肉过敏,他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不无遗憾地说:“哎!那你可错过好东西咯!我们进的羊娃子,可是喝雪水长大,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啊!”见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又赶紧纠正说:“没事,虽然比不上羊肉串,不过咱这牛肉串也好吃。”
小孩子的好奇心似春天的种子,总是一股劲地从地里往外蹿。有回等串时,我忍不住问:“大叔,你这个外地人咋跑到我们这儿来卖串呀?”
他正往烤炉里添炭,火星子映得胡子发亮。听我一问,他转头看向阿姨,眼角皱纹堆成葡萄干,笑眯眯地和我解释:“你阿姨是这里人,当年她在我们那里闻着我烤串的味儿人就走不动了……我就跟着她到了这里咯!”阿姨始终坐在一旁穿串,闻言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只是有几分得意,嘴角轻轻往上翘。
大叔烤串特别讲究,其他摊主拿塑料瓶撒调料,而他偏要戴上一次性手套,抓捏一把孜然和盐在掌心揉匀,手腕一抖,细雪般的调料就均匀地裹上肉串了,夕阳下,焦黄焦黄的烤串上像是撒了一把碎银。
有次我盯着他手上的烫疤出神,他忽然得意地晃了晃说:“这可都是勋章啊,当年追你阿姨时,为了练这烤串的手艺,没少被炭火烧。”阿姨在一旁听了,耳尖微微发红,起身朝大叔的搪瓷杯里添了水,拿起毛巾给他擦了擦汗。
烤炉腾空的烟雾裹住他们夫妻两人,溢出的是平淡的幸福。
我想那油润的牛肉串里,藏着的不只是恰到好处的咸香,更是大叔撒调料时,眼角扫向阿姨的温柔与爱意。
后来我长大了,很少去那条老街。可前不久回家,听闻那条老街却要拆掉了。
我忽然想再去一次老街,走走那些坑洼的青石板路,再吃几串大叔烤的牛肉,就像从前无数个放学的下午那样。
踩着一路黄昏,我到了老街。大概是我到的时间比较晚了,校门口早就没了学生的身影。顺着记忆中的方向慢慢走着,脚下的石板路还是坑坑洼洼,每走一步都能勾起许多回忆。转过街角,那熟悉的摊位映入眼帘,奇怪的是,曾经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烤串小摊,如今只剩下一片空地。
是搬走了吗?我的心往下一沉。就在准备离开时,忽然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孜然香,我心中一喜,循着气味找去。走到老街另一头相对偏僻的角落,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是那个卖烤串的摊主大叔。
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依旧是深灰的铁皮推车支着褪色的橙红帆布棚,他依旧围着那条沾着油渍、洗得发白的蓝围裙,戴着一次性手套,正熟稔地翻动着烤架上的肉串,肉串在炭火上吱吱冒油,孜然与牛羊肉的香气混着炭火的焦香扑面而来。
我像从前一样开口要了几串牛肉。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大叔头发与脸颊周遭的一圈胡子不知何时染上了霜雪般的盐粒,很是沧桑。而且,再也不见阿姨低头默然穿串的身影。
我犹豫片刻,轻声问:“阿姨今天没过来呀?”烤炉腾起的烟雾迷蒙了大叔的眼,泛起了一层水雾,他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两年前走了,病没扛住。”他顿了顿,仿佛回忆漫过心头,缓缓地说:“她最爱吃我烤的串了。”
不知怎么回事,我喉头突然一紧,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我轻声地说:“这么多年了,我总惦记着您这烤牛肉串的味道。”大叔愣了一下说:“丫头原来是你呀!”他将烤好的牛肉串递给我,有些莫名:“这里要拆迁了,说好要吃一辈子我烤串的人也走了……是啊,我该歇歇了。”
接过烤牛肉串,我咬下第一口时,那股熟悉的香味瞬间就在舌尖上绽放,似乎味道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只是多了些难以言喻的、不一样的滋味。
那个曾陪在摊主大叔身旁、埋头穿串的身影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而这个小小的、仅有三平方米的烤串小摊,却终将随着拆迁的步伐,封存在时间的褶皱里。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