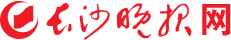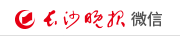一座山的浪漫与邀请
余孟孟
一支笔要经过多少历练,才能写出一座文化名山的万年风华?
著名作家孙犁在《书林秋草》中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写好文章”。划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万年青翠》,正是这样一部书写长沙岳麓山文化底色与生命气象的力作。
作者黄耀红在跋中坦言:“无论如何书写,都只能表达对岳麓山的谦卑与敬意。”这份谦卑绝非虚辞,而是学者的心灵独白。作为求学、执教皆在岳麓山下的湖湘文化学者,黄耀红集大学教授、传媒达人、人文学者于一身,始终以岳麓山为精神母题。这座山滋养了他的思想根系,而他以笔墨反哺,堪称当之无愧的“岳麓山之子”——正如他所言:“岳麓山是文化之父,精神之母。”
正是这份人山相守的情谊,《万年青翠》超越了自然科普与山水美文的窠臼。全书40篇分五辑展开:山水相依、人文互见、草木四时、众生平等、清欢有味。文字如墨晕染,勾勒出岳麓山一木一亭;如弦震颤,交响着林泉鸟语;如料烹鲜,烩制出古今传奇。展卷如观水墨长卷,掩卷仍有清音绕梁。
观岳麓,是观其自在、自律与自愈。
天地赐予“岳麓八景”,奔涌的湘江,灵动的流泉,皆为造化自在之美。草木荣枯更显自律:春桂含芳报信,秋枫燃火作笺,六朝松凝视岁月更迭,千年银杏见证善恶轮回。当冰雪摧折漫山青翠时,谷雨后重生的葳蕤新绿,则昭示着土地深处永不衰竭的自愈力——这种力量,既源于护林人的耕耘,更来自大山自身倔强的根脉。作者曾见满目疮痍的山林“在伤痛里呻吟”,却在春日见证“被春天治愈的奇迹”,正是这自愈力的生动注解。
听岳麓,是听青山之音、青史之声与青春之歌。
石铭刻着大禹治水的传说,泉流淌着朱熹张栻的辩难,密林间回荡谭嗣同“去留肝胆”的绝唱。作者以“青”为文眼,奏响万年青翠的交响:古麓山寺晨钟暮鼓是低音部,爱晚亭飘落的枫叶是轻颤的琵琶音,而毛泽东蔡和森登山咏怀的足迹,则是激越的青春强音。胡宏“为是青山青不老”的诗句在此得到印证:从蔡锷松坡墓的剑胆,到今天网红长沙的创意灯火,岳麓山的青春密码,正藏在代代湖湘子弟“敢为天下先”的血脉里。
品岳麓,是品其文辞、文化与文心。
历代文赋构建起文学风骨,儒释道三家在此和而不同:岳麓书院传续经世济民的火种,麓山古寺坐看红尘起落,云麓宫吞吐天地灵气。这种文化共振滋养出独特的精神图谱——赫曦台的晨光既照亮“惟楚有材”的匾额,也映着青年学子“实事求是”的沉思;朱张古道的石阶既印过先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足迹,也见证着当代人“亲山水、向文化、尚闲适”的生活诗篇。正如作者所言,这里每处景致都是“人心、地心与文心的精神同构”。
《万年青翠》作为“致敬岳麓山三部曲”开篇,与谢宗玉《千年弦歌》、王开林《百年群英》形成互文:草木见芳华,文脉显性格,人物现肝胆。三支妙笔共同勾勒出名山的精气神——既是“精神共同体”的万年之风,亦是“文化交融体”的千年之雅,更是“生活建构体”的百年之颂。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