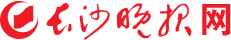从“杀年猪”到“赶屋场”的乡愁

邓志刚
当算法精准推送给你消费日常,当外卖可以一键解决三餐四季,那些需要等待、需要亲手参与、需要邻里协作的温度,却愈发成为现代人心中渴盼的乡愁。
或许,这便是为何一段重庆合川“摇人按猪”的短视频能迅速走红,也是为何在长沙县开慧村,一场传统的杀年猪仪式,能将我这个外乡人的脚步牢牢钉在原地,瞬间拽回那段混合着柴火气、猪嚎声与邻里笑语的遥远年关。
小时候,杀猪师傅是村里腊月最风光的人。母亲曾半开玩笑地说:“学杀猪吧,有肉吃,还受四里八方尊重。”那确是一门关乎尊严与生计的手艺。而今,在开慧村的这户农家,同样的忙碌上演:有人拍照发圈,有人抖音直播过程,更多人一拥而上,手忙脚乱地按住奋力挣扎的年猪。沸腾的喧闹中,时光的滤镜被猛然擦亮。
儿时记忆涌出。天未亮就被唤起烧水,跑去邻家“捎信”请人“扯猪”。鞭炮炸响,母亲向着从祠堂请来的伯公塑像恭敬作揖,口中念念有词。那塑像怒目圆睁,眉头紧皱,幼小的我甚至不敢直视,只觉得一种肃穆的庇佑笼罩着这场盛大的劳作。后来明白,那不过是寻常人家对风调雨顺、岁丰年稔最朴素的祈求。
将猪拖上门板是最高潮,也最紧张。母亲念叨过的忌讳言犹在耳:曾有猪挨刀后带血狂奔,那家人来年便觉事事不顺。这或是迷信,但“霉头”带来的心理暗示却真实不虚。于是,邻居们无不火力全开:扎马步,绷腰身,手背青筋暴起,有人几乎整个身子扑压在猪身上……此刻,猪嗷嗷叫个不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抵抗着。直到屠夫眼疾手快,白刃进,红刀出,一股热血喷涌,那挣扎的躯体才渐渐瘫软。众人歇口气,空气里紧绷的弦陡然一松。
随之而来的,是轻松的说笑与手艺的展示。分解骨肉时,邻里间互相打趣着刚才谁更卖力;屠夫则展现“庖丁解猪”的利落,刀尖暗劲吞吐,匀整的猪皮便与肉身分离。我曾痴痴看着听着,听说猪皮都拿去给城里做皮鞋了,便梦想着有一天能穿上自家猪皮做的鞋。梦想还未成形,就被催去烧火——卖猪肉的钱,是我和妹妹的学费来源。
“杀猪宴”是这场仪式最温暖的句点,更是对汗水与互助的犒赏。就地取材胜在一个“鲜”字,辣椒炒肉油亮喷香,爆炒猪肝嫩滑无比,肉丸汤鲜美滚烫,猪杂炖锅热气腾腾……食材的鲜,在那一刻直抵舌尖、沉淀心头。这顿饭,既答谢邻里援手,也慰藉家里人剁猪草、拌猪食的辛劳。
记得有次,我被慌乱的猪踩了一脚,疼出眼泪却仍往前凑,想着马上就能“报仇”。等大伙按住猪,我也奋力抓住一只猪脚,仿佛那微小的力量,能换来理直气壮多干一碗饭的资格。
“先生,外地人吧?”开慧村主人的询问将我拉回现实。见我入神,他热情相邀:“留下吃杀猪饭吧!如今日子好了,肉随时能买,但家里每年还是坚持杀年猪,自己留些,多的分给乡亲。”我欣然点头。是呵,一头年猪,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是夏耘冬藏的实收兑付,是乡土社会人情网络的生动纽带。在年味被稀释的时代,这场盛宴唤醒的,是关于团聚、人情与烟火气的集体记忆。我们奔赴的,不止是一餐饭,更是一场情感的认领与重温。
我注意到,新时代的“杀猪饭”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它成了网络引流的起点,像一根金线,串起散落乡镇的珍珠,颇有小时候过年走家串户赶屋场的闹腾感。过去的“赶屋场”,是家家户户拜年问好。而如今,村里人开着小车穿梭走亲,更多时间则在迎接八方来客。城里人反向来到村里“赶屋场”了。从开慧故居、初恋茶馆,到开慧小学和杨公庙一线,打年糕、做花灯、捏糖人等摊位前人头攒动。红色的信仰故事与古老的年俗传统,在这里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充盈的幸福感。
返城时,我带上了几斤鲜肉,那温热的触感,仿佛携着童年的余温,伴我踏上归途。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