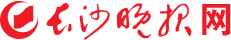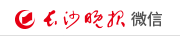儿时院子里的浓浓“年味儿”
文│张依然
时钟嘀嗒,年的脚步已至。记忆里围合的院落,是家人团聚的符号。穿新衣、写福字、撑灯笼……每一项仪式背后,承载的都是中国人对传统中国年的一份期盼。
“年味儿”这东西摸不着、说不清,每个人对新年的感受也各不相同。季羡林说,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
是的,新的一年又随着这“轻轻一拂”而姗姗来了!然而,忙碌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忽略了时间,久违的“年味”也没有了往日的浓郁。这让我不由得回想起小时候,在大院里过年时的喜悦与童趣。
那时候的长沙没有那么多人,我们住在车站北路225号蓉园小区的院子里。每到过年,院子里早早贴上了春联,各个办公大楼前门厅悬挂着大红灯笼,树上挂上了灯带,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灯光交相辉映,这一丛,那一簇,层层叠叠,浓淡纷呈,点缀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变得诗意盎然,处处洋溢着过新年的祥和景象。工会的大活动室里,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写对联、画福字……满屋子都弥漫着浓浓的墨香味,好多家属排着队的等,有种如获至宝的喜悦感。
那时候的五一路、蔡锷路、阿波罗广场、王府井百货、友谊商店,都是过年前必去的打卡点,很多年货也是从那里置办来的。过年前,我就开始惦记着家里储藏室的零食,趁着家人都出去的功夫,我总会想尽办法找到钥匙,然后进去扫荡一圈,再把翻过的零食包装恢复成没有动过的样子。即便这样,有一次,还是因为拿多了我心头爱——巧克力瓦夫和果丹皮,被姨妈发现后,罚我拖地,哥哥在旁边不停地做鬼脸,我心里那叫一个气!暗自想,等我长大了,一定买好多好多的零食,放在我的床头柜里,再也不用因偷吃被罚了。
而今,我终于长大了、工作了,也实现“零食自由”了,再也不用偷吃年货里的零食了,但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吃零食时的幸福感了。重温记忆中的浓浓年味儿,便成为了我最真切的向往。
那时候姨妈还很年轻,和院子里很多爱美的阿姨、姐姐一样,过年前一定要去做个新发型,院子里的理发师自然也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小孩子最关心的是一套崭新的衣服,一对漂亮的发夹。那时候,过年的新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承载着父母的爱与期盼,包裹着孩子们对新年的美好憧憬,也成为70、80后心中永不褪色的“年味儿”记忆。那时候,城里还没有禁止放鞭炮,家家户户都会置办烟花和爆竹,三十晚上也会一家人围坐一起,开开心心的守夜,放烟花,许心愿,盼望着新的一年长得更高、吃得更好、过得更韵味。春晚看到一半,大院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大家闻声都聚到院子里烟花燃放点,各家各户的烟花都摆放在了一起,在夜空中竞相绽放起来。五彩缤纷的烟花,邻里间的祝福与笑容,让整个院子都沉浸在欢欢乐乐过大年的氛围里。我们女孩子便会按捺不住的戴上漂亮的发夹,提起纸灯笼去院子里玩耍,大院的男孩子喜欢用“摔炮儿”袭击我们的灯笼,一不留神,“啪”的一声,好看的灯笼就被点燃,化作一团火光,看着我们哇哇大哭,男孩子们雀跃着逃到樟树下、柳树丛里躲起来……至今回想起来那时那景,都觉得甚是有趣。
湖南人过年当然离不开腊味,有人说在湖南不吃腊肉就不像过年,我们院子里也是如此。一走进蓉园住宅小区,早早就闻到了腊肠、腊鱼、腊鸡、腊鸭、红烧狮子头的香味儿,楼上楼下也会在年夜饭前把餐桌上的美食送来送去,你送我一碗腊肉与冬笋、我回你一碟糖油粑粑,你给我一盘梅菜扣肉,我敬你一碗手工水饺……朴素的仪式感中,弥漫着浓浓的幸福感和十足的人情味。
最期待的还是初一早上拜大年。在那个物质不充裕的年代,一年到头买不了几件新衣服,孩子们全把希望寄托在了过年这一天。新衣服总是早早地购置好,藏在衣柜里,那份喜悦与期待在等待中愈发强烈。直到除夕之夜,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将新衣服从衣柜中取出,整齐地摆放在床头,那份期盼之情达到了顶点。一夜好眠之后,清晨时分,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穿上这一身全新的行头,那份由内而外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属于我们的年味,就藏在诚意满满的饭菜里,藏在热热闹闹的烟花里,藏在欢欢喜喜的全家福里。那墨香与纸香混合的独特气息,那交换年夜饭的热闹场景,那给院子里长辈们拜年后抽屉里的红包和糖粒子,就是童年里新年最温暖的味道。
岁月流转,那些院子里的春节趣事依然是心底最美好的回忆。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味儿或许淡了些许,但那份深藏在记忆中的温暖与快乐,却永远不会消逝。它就像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成为我们心中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从前没有手机没有WIFI,但新年却过得很开心。只要回想起儿时过年的点点滴滴,那份纯真的快乐便会重新涌上心头,温暖着长大后的每一个寒冬。愿我们都永远珍藏记忆里的童趣与纯真,开启新春的序曲;愿我们珍惜大院里的这份传承,将“年味儿”继续传递给下一代,让春节的美好永远延续;愿新岁胜旧年,我们心怀热爱,一路生花!我们欢欣此时,也遥望未来!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