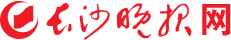散文 | 屈原之心结
王开林
世间很少有一种节日的标配熟食会遭遇粽子的苦况,赴汤蹈火之前,先要“披枷带锁”。
小时候,我在家中见过母亲和姐姐包粽子,从搪瓷盆里勺出半杯雪白的糯米,倒进两片折成牛角形的青青箬叶中,置入一颗不大不小的红枣,然后上下其手,将它包个严严实实,再拿麻线捆紧扎牢,一只棱角分明的粽子(难怪古人称之为“黍角”)就像变戏法一样变了出来。
粽子下锅,经沸水煮熟,食用时,轻解罗裳,通体如玉,五官都会被它吸引和征服,眼观其美色,鼻嗅其清香,口舌尝其妙味,可谓皆大欢喜,耳朵能够干吗?当然是倾听食客对粽子的品评和点赞。
俱往矣,这是多年前的情形才对。现在的孩子,贪吃巧克力、冰激凌和西式糕点,嫌粽子的模样土气,都不愿多看它一眼,更别说欣然启齿了。说轻点,娇生惯养;说重点,就是数典忘祖。
不管你吃不吃粽子,屈原都在泽畔行吟,虽死犹生。有人说,他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空前绝后的行为艺术家。一个男人(不管他是不是诗人)投水自尽不难,事先张扬也不难,但屈原将自己的忌日变换成传统节日,将自己的精神遗书(《怀沙》)转化为千古绝唱,这本事,就算东方不败挥刀自宫,将葵花宝典上的神功悉数练得炉火纯青,也无法望其项背。
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边纵身一跃,根本不像是坠落到了水中,倒像是飞升到了天际,地心引力完全莫奈他何。老百姓担心屈原的尸体被鱼虾吃掉,起初是将粽子扔入江中,嗣后是将粽子塞入口中,这样的善意,屈原笑领了两千多年,仍未厌倦。
某年,我参加庐山笔会,适逢端午节,聊起屈原,有人就像是老庙里的火头僧专参野狐禅。最奇怪的说法是:“屈原对楚怀王念念不忘,至死忠心耿耿,我猜想,他很可能已经出了什么毛病,否则就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战国时期,纯粹的爱国主义尚未提上士大夫的议事日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论是谁,周游列国都不用办理签证,天才到处受欢迎,没人肯钻死胡同。那年月,本事大的,比如苏秦,竟然腰悬六国相印,他的师弟张仪也是一会儿腰悬秦国相印,一会儿腰悬魏国相印,他们热爱的可不是哪个国家,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金钱。”大家听罢怪论,一笑了之。倘若从“一切皆有可能”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似乎成立,但也有较真的,辩驳道:“战国时期,士大夫爱国确实不是普遍行为,正因为这样,屈原近乎绝望的爱国精神就更加如同空谷足音。”戏说与正论并没有发生激烈交锋,私下场合,各抒己见,不会伤及和气,更不会影响大局。
你用什么东西堵我的嘴,我都会表示反感,但是你选在端午节用又香又软的粽子堵我的嘴,我就无话可说了。多少人阅读过完整的《九歌》和《九章》?中学课本曾收录了一首《国殇》,五十岁之后仍能够背诵它的人就不会患上健忘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诗被广泛征用,却没有几个聪明人肯把密不透风的《离骚》读得眉目疏朗。屈原的知名度奇高,说是家喻户晓,一点也不为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不是与楚辞联系在一起,而是与端午节的粽子打成一片。初想想,好玩;细想想,则有些深意。
还记得《渔父》中的名句吗?“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一度想开了,也想通了,遇到无可救药的浊世,洗脚上岸才对,怎么又投水自尽了呢?屈原之心结犹如死疙瘩,如果他无法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岸就比彩虹更为虚幻,他用浊水洗完了脚,仍旧报国无门,有家难归。于是他投入一派清流,索性做个了无牵挂的“波臣”。
楚国亡了,但其形象代言人屈原永垂不朽,幸与不幸,还真不好轻易断言。但屈原要的是实惠(楚国长盛不衰),而不是虚名,可惜他没有选择权,选择权掌握在命运女神的手中,不肯让渡,她更乐意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那天观看一场激烈的龙舟大赛。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