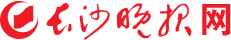散文 | 戴艾叶的小女孩
李文丽
五月,草木丰盛。溪流边,小路旁,山坡上,一丛丛艾草肆意生长,青葱繁茂,羽状的叶片上覆盖着细腻的淡淡的灰白色绒毛,艾草的香在初夏阳光的抚摸和雨水的滋养中愈发醇厚。祖母说,艾草成熟了。
端午节的清晨,薄雾四起,晓风微凉,布衣青衫的祖母拿着弯刀,踩着露水,去野外割艾草 ,一捆捆抱回来,插在门两边的墙缝里,长长的艾草低垂着微微弯成一个弧度,艾草的香幽幽地散开。家家户户挂艾草,为端午节装点了节日的气氛,传说中端午节挂艾草有避邪祈福的作用。等艾草干枯了,收起来,搁置在房架上,以受烟火的熏蒸。端午节收集的艾草,可以杀菌消毒,除疼止痛,平日里有个小毛病,都是用它来熬水喝。
祖母割艾草时,我喜欢跟着,这时候祖母总会摘下几片艾叶, 戴在我的头上。她说,端午节头上戴艾叶,能避邪杀毒,保这一年都不会生疮长包结。我对这种说法半信半疑,对戴着艾叶却颇有兴致,那样朴素而单纯的年代里,有那么一天,能过得和平常不太一样,令人非常兴奋。头上戴的艾叶,在我小小的心中,不仅是习俗,也是一种装饰,一种为节日加冕的欢乐。
端午回忆的馨香里,除了艾草的药香,还有粽子的清香。比起吃粽子,包粽子更有乐趣。山后的那一片半人高的粽竹林枝繁叶密,一片片小舟似的叶簇拥着,在五月的风里吟唱着“沙沙”的歌谣,祖母扒开竹枝,麻利地摘下一片片粽叶。我去摘,却被粽叶锋利的边缘划伤了手指,不免被祖母说上几句,末了抹上一点泥巴了事。我却并不因此循规守矩,又折断几根竹枝,拿在手里舞啊舞,不亦乐乎。
粽叶采来了,在清水中漂洗后,放在筲箕里沥干水,一片片粽叶清莹莹的,闪着翡翠般的光。包粽子是个技术活,泡好的糯米混着绿豆被祖母用勺子装进粽叶折成的“小角斗”中,再把粽叶包起来,用棕树叶撕成了短绳缠起来,一个四个角的粽子就包成了。我在旁边学着,虽包出来的粽子奇形怪状,但并不影响我欢乐的心情。
粽子包好了,几个结成一串,放入锅里煮。不一会儿,热气从锅盖的边缘冒出来,带着粽叶特有的草木清香,糯米的甜香,一缕缕在空气中流窜。祖母打开锅盖,沸腾的香味四散开来,馋得人口水直流。我用力吸着鼻子,任粽子的香沁入心田。一串串粽子从锅中提捞起来,在祖母的手上晃动,然后又被沥在筲箕里。祖母包的粽子,除了自家人享用,也会给左邻右舍没包粽子的人家送一些,那些年的端午,就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悄然而过。
端午闻香——艾草的香,粽子的香,回忆的馨香,从时光的深处飘来,散不去。那戴艾叶的小女孩,布衣青衫割艾草包粽子的老人,那些古老的习俗,都被定格在记忆中。如今,居住在城镇,各种口味的粽子应有尽有,但是我总觉得亲手包粽子才有过节的仪式感,那是属于乡村独有的,是自然和节日馈赠给人们的喜乐时光,只可惜,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要举报